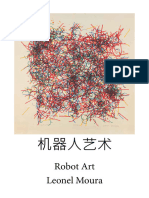Professional Documents
Culture Documents
跨文化原典导读
跨文化原典导读
Uploaded by
zyz10714212330 ratings0% found this document useful (0 votes)
4 views2 pagesCopyright
© © All Rights Reserved
Available Formats
DOCX, PDF, TXT or read online from Scribd
Share this document
Did you find this document useful?
Is this content inappropriate?
Report this DocumentCopyright:
© All Rights Reserved
Available Formats
Download as DOCX, PDF, TXT or read online from Scribd
0 ratings0% found this document useful (0 votes)
4 views2 pages跨文化原典导读
跨文化原典导读
Uploaded by
zyz1071421233Copyright:
© All Rights Reserved
Available Formats
Download as DOCX, PDF, TXT or read online from Scribd
You are on page 1of 2
浅谈“模仿”的生活与“真实”的界限
张钰泽 102062021195 基地班
在希腊古典时期的模仿说中,无限接近被模仿物被奉为神圣的准则。在文艺创作
中,创作者们以自己反映的“真实”为傲,然而文艺作品中展现的主体,是在作品诞
生后与之藕断丝连的“叙事者”;而接受的客体——观众,则处于被动位置,观者摄
取全面真实的权利难以避免地被掠夺。所谓真实变成了意图的修辞,所谓客观变成人
们幻想的理想。当呈现“全面的真实”成为创作者们标榜“实验”、“先锋”的利器
时,滥用造成信息过载的负担,善用亦会导致“经典化”,造成观者的审美疲劳。当
“真实”从追求精确模仿的神圣到寻找自我与世界的连接,所谓模仿的生活才到达了
真实。
古时的模仿多关系到诗,强调精确的再现,机械复制多关系到视觉艺术,接近于
科学再现,未来的拟真则以丰富的感官体验,给我们创造一个超现实的世界。“真
实”变得触手可及,真实的崇高感亦被消解,且以高效、便宜的优点,被更快地制造 。
原来的接受者变成了创作者,从被动、消极的传播对象变成主动、积极参与的传播主
体。以短视频为首的现代媒体颇有野心地挖掘新奇事物,人们从书面传播时代保留的
想象力几近耗竭。正如快手的那句广告词,“快手,看见每一种生活”。在鲍德里亚
悲伤的论调中,媒介自身已经包含着封闭的主动的完整话语,观众的回应被先行规定 。
在高行健看来,“生活中并非只有情节,还有许多非情节的因素”。若要重新拾起
“真实的感觉,便需要在日常的表象之下触碰生活不可复制的本质。
在大多源于生活、高于生活的文艺作品中,创造者总是占据主动地位,查特曼认
为叙事者/呈现者是“隐含作者”,“他创造事件、人物和对象(故事),并创造这一
切被传达所用的方法(话语)。叙述者是话语代理,负责呈现语词、画面或其他传达
该意图的信号”。即使是以高度真实的视听语言引导读者参与文本世界的电影亦然,
在集中且开放的叙事画面,叙事者依托媒介的综合性运用多种手段,包括剪辑、画外
音、音效、灯光等等,凝练矛盾,决定呈现谁,遮蔽谁。观众所看到的一切,正是隐
含叙事者依据某种理念或欲所要呈现的状态。但是呈现者大方让渡出的“全面真实”
就一定真实吗?2008 年,在复刻现实生活的电影《纽约提喻法》中,查理·考夫曼试
探作品与生活的边界,使镜头“完全客观”地对准电影中导演的生活,电影中的导演
亦将自己的生活绝对地复刻到戏剧中,甚至大便的颜色、私人化的性生活等都被搬上
舞台。被截图式纳入戏剧的生活细节、日常与偶然都被历史永恒化,然而它们构成了
这部名为“人生”的戏剧的血与肉,却无法拥有灵魂,因为这是极度自我的人生。当
他使紧紧跟随、观察他数十年的扮演者代替自己与情人交往时,生活显露出它的无边
无际,因为他试图在把真实的自我放入戏剧生活,却“除了你自己,你从来没有真正
看过其他人”。所谓的“全面的真实”只是自己建构的内心世界的复刻。那些无法进
入历史、亦被现实淘汰的种种生活细节,进入被微缩的时间、被微缩的城市、被微缩
的人与人之中。2022 年内森的类纪录片《彩排》进一步触碰生活的边界,当一件事尚
未发生时,事无巨细地设置真实事件发生的条件,模拟真实中人的情境与反映,顾及
种种影响因素,彩排人们在生活中纠结的种种事情,总难以避免,有一种可能性,是
无法模拟的。因为生活中有太多偶然性和意料之外的因素。实验场中,内森到处设置
记录每一种反应与可能的摄影机,然而摄影机仍是隐喻,类似“隐含叙事者”,使人
在真人秀中扮演一个有明确结局倾向的角色。于是隐含作者在看似开放的故事中又编
织了自我封闭的,且十分自洽的网,脱离了生活的偶然性,无法到达真实,终只是个
“秀”。
柏拉图认为戏剧式转述是“完美模仿”,人物话语(常常是人物的个体语言记录
或是对话)被不加修饰地呈现给读者。正是这种潜意识的自然流露,使得冲突、人物
关系等都被隐藏于简短语言下巨大的冰山,且高度集中地围绕与服务于某一“理念”。
易卜生多创作接近真实的写实剧,他认为“戏剧效果应该是让观众真实地体验一段真
实的生命历程”。而被称为“新易卜生”的福瑟走向极简主义,走向另一种“真实” 。
他的戏剧将人物放置在离大海无限近的人类社会的“边境”,诉说不可言说的境地。
在《Someone is going to come》里,将自我封闭的两个人来到无边无际的自然空间,
难 逃 身 上 携 带 的 社 会 记 忆 。 尽 管 男 人 一 直 回 答 “ No-one else” , 女 人 亦 害 怕
“someone”,直到一个男人闯入他们封闭的空间,所有基于此前经验的猜测,都使得
“she”和“man”的偶然相遇变成了蓄谋已久的约会。直到结尾回归沉默,观众不知
道两人的未来何去何从。正是生活中大量的偶然性因素,使得每一天,都可能“有人
将至”,任何外来因素都可能影响人的生活,甚至改变人的命运。福瑟习惯于将“先
行事件”被隐去,只留下最初的人物的关系——情侣,构建极度开放的“情感的框
架”,或某种“人类的处境”。在角色的不确定与人物命运的不确定中,导演、演员、
观众都可以在“he”、“she”、“man”三角关系的“框架”中装进自己的东西,从
而感受到自己与戏中人的联结,获得感受上与内在心理上真实的统一。
综上讨论,生活正是充满着许多偶然,正是这个偶然,使得文艺作品模仿的生活
的“真实”与现实的“真实”之间蒙上了朦胧而又神秘的屏障。在疫情的不确定中,
互相隔绝的生活突出了虚拟交流体验的时代价值,元宇宙的真实构造于真实世界的交
际,人们共情、共建、共生、共享。当真正摆脱物质的束缚,按既定经验编码好的程
序将模拟“真实”的感觉,那么生活的“偶然”该去向何方。
You might also like
- 《跌入恐惑谷:远程机器人艺术研究》Document15 pages《跌入恐惑谷:远程机器人艺术研究》bingwan zhang100% (1)
- 触摸图像的话语及其临界 赵阳Document10 pages触摸图像的话语及其临界 赵阳XUNo ratings yet
- 当代艺术与视觉文化 主题2Document45 pages当代艺术与视觉文化 主题2Lixiao FengNo ratings yet
- 瓦萨里艺术思想中的"模仿自... -通往一种艺术史写作的路径 卓敏Document11 pages瓦萨里艺术思想中的"模仿自... -通往一种艺术史写作的路径 卓敏zjrlareinaNo ratings yet
- 視覺藝術報告Document2 pages視覺藝術報告陳筠喬No ratings yet
- 視藝大崗Document9 pages視藝大崗陳筠喬No ratings yet
- 雾中风景:"废墟"意象中的断裂与遮蔽Document15 pages雾中风景:"废墟"意象中的断裂与遮蔽程海逸No ratings yet
- 浅析观众沉浸感和博物馆沉浸式展示要素 张琰Document8 pages浅析观众沉浸感和博物馆沉浸式展示要素 张琰yilia leeNo ratings yet
- 从虚拟现实到虚拟成为现实-... 宇宙"与艺术的"元宇宙化" 周志强Document4 pages从虚拟现实到虚拟成为现实-... 宇宙"与艺术的"元宇宙化" 周志强林林No ratings yet
- 从贡布里希视知觉论看中国形神画论生态演变 高尚学Document6 pages从贡布里希视知觉论看中国形神画论生态演变 高尚学GabrielzyxNo ratings yet
- 麦克卢汉媒介感知理论视域下的VR纪录片探析 肖湘宁Document5 pages麦克卢汉媒介感知理论视域下的VR纪录片探析 肖湘宁Great MindsNo ratings yet
- 目光的相遇与灵韵的回归:本雅明摄影理论再审视 黎江波Document6 pages目光的相遇与灵韵的回归:本雅明摄影理论再审视 黎江波1459626991No ratings yet
- 3、本亚明: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(1 6章,每章都很短,有兴趣的同学也可自己看其它章)Document201 pages3、本亚明: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(1 6章,每章都很短,有兴趣的同学也可自己看其它章)王浩No ratings yet
- 现实主义中的身份预言Document7 pages现实主义中的身份预言2356609040jyNo ratings yet
- 论前卫艺术的哲学感 以"物"为核心 - 吴兴明Document15 pages论前卫艺术的哲学感 以"物"为核心 - 吴兴明王靖善No ratings yet
- 人体之美 西方人体素描绘画研究Document3 pages人体之美 西方人体素描绘画研究2022 supperheroNo ratings yet
- 论摄影文学的艺术 冯政博Document1 page论摄影文学的艺术 冯政博Charlotte WangNo ratings yet
- 论叙事视角 张闳Document11 pages论叙事视角 张闳Jiho KimNo ratings yet
- 在栖居中超越图像的时代Document16 pages在栖居中超越图像的时代程海逸No ratings yet
- 真理的辯證與呼喚Document6 pages真理的辯證與呼喚dochdochNo ratings yet
- 超真实、拟真与内爆 后期鲍德里亚思想中的三个重要概念Document8 pages超真实、拟真与内爆 后期鲍德里亚思想中的三个重要概念向子晗No ratings yet
- 模仿的動力 黃聖哲Document11 pages模仿的動力 黃聖哲Tan Choon TingNo ratings yet
- 论艺术真实之维 张新艳Document5 pages论艺术真实之维 张新艳1500620274No ratings yet
- 图像的辩证乔治·迪迪 于贝尔曼对极少主义的图像阐释Document5 pages图像的辩证乔治·迪迪 于贝尔曼对极少主义的图像阐释fuanjie233No ratings yet
- 从媒介隐喻的视角审视波普艺术 林芷含Document4 pages从媒介隐喻的视角审视波普艺术 林芷含yangmeiyangmeiyangmeiNo ratings yet
- 从"面"到"界面" 数字技术时代的艺术史书写 - 徐书琪Document4 pages从"面"到"界面" 数字技术时代的艺术史书写 - 徐书琪tingyuanNo ratings yet
- 阿尔伯蒂的现代性 读《论绘画 阿尔伯蒂绘画三书》Document2 pages阿尔伯蒂的现代性 读《论绘画 阿尔伯蒂绘画三书》徐磊No ratings yet
- 历史真实与舞台真实 - 从大 代吕剧《回家》人物造型谈起 - 潘健华Document5 pages历史真实与舞台真实 - 从大 代吕剧《回家》人物造型谈起 - 潘健华1500620274No ratings yet
- 贾科梅蒂的眼神 从现象学角度看现代艺术Document2 pages贾科梅蒂的眼神 从现象学角度看现代艺术siukei yuNo ratings yet
- Robot Art Leonel MouraDocument83 pagesRobot Art Leonel MouraepicpinnNo ratings yet
- 从异面看同相 关于艺术与科学 周宪Document10 pages从异面看同相 关于艺术与科学 周宪Larry ZhangNo ratings yet
- "摹仿自然" - 论人类创造性观念的前史 汉斯·布鲁门伯格Document46 pages"摹仿自然" - 论人类创造性观念的前史 汉斯·布鲁门伯格JF catNo ratings yet
- 后科幻写作的可能 关于王威廉《野未来》 - 杨庆祥Document3 pages后科幻写作的可能 关于王威廉《野未来》 - 杨庆祥zhoulegejiuNo ratings yet
- 中国当代艺术中的 废墟 描述及其 省略 东 三峡大移民 三峡新移民 为例 金丹元Document7 pages中国当代艺术中的 废墟 描述及其 省略 东 三峡大移民 三峡新移民 为例 金丹元李雨恒No ratings yet
- - 否定性与乌托邦 - T J 克拉克的现代艺术史观的核心Document8 pages- 否定性与乌托邦 - T J 克拉克的现代艺术史观的核心Fan NieNo ratings yet
- 挑战"创造性":人工智能与艺术的算法 王峰Document10 pages挑战"创造性":人工智能与艺术的算法 王峰Jiu LiNo ratings yet
- 论席勒美学中的自由观念 孙健风Document3 pages论席勒美学中的自由观念 孙健风泽恩 吴No ratings yet
- 非虚构影像 证据与修辞之间 孙红云Document9 pages非虚构影像 证据与修辞之间 孙红云fuanjie233No ratings yet
- 从"太空歌剧"到"赛博朋克... 下科幻美术题材的发展与演变 金阳Document2 pages从"太空歌剧"到"赛博朋克... 下科幻美术题材的发展与演变 金阳ylu870301No ratings yet
-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"德勒兹与鲍德里亚现代性批判比较研究" (项目编号 13CKS032)阶段性成果,也得 到了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( 2013/B13020334和2013/B14020223)资助。 (1) 〔法〕德波: 《景观社会》,王昭风译,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,第49页。Document8 pages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"德勒兹与鲍德里亚现代性批判比较研究" (项目编号 13CKS032)阶段性成果,也得 到了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( 2013/B13020334和2013/B14020223)资助。 (1) 〔法〕德波: 《景观社会》,王昭风译,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,第49页。allenevan620No ratings yet
- 应然与实然的互动Document9 pages应然与实然的互动3031431800No ratings yet
- 复数的瞬间:"刺点"中的时间机制 吴娱玉Document10 pages复数的瞬间:"刺点"中的时间机制 吴娱玉1234No ratings yet
- 人类学的影视表现:从保存到展现Document9 pages人类学的影视表现:从保存到展现y.h.chuang y.h.chuangNo ratings yet
- "元宇宙"之自我生境的"元... 世界间的"自我认同"之论析 张亮Document11 pages"元宇宙"之自我生境的"元... 世界间的"自我认同"之论析 张亮Min chenNo ratings yet
- 大學國文補充教材 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Document9 pages大學國文補充教材 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benjamin chen (lightning kite)No ratings yet
- 假如元宇宙成为一个存在论事件 赵汀阳Document11 pages假如元宇宙成为一个存在论事件 赵汀阳Han RenhaoNo ratings yet
- 山脉、地层与矿物:实验影像中的地质转向 杨北辰Document8 pages山脉、地层与矿物:实验影像中的地质转向 杨北辰王涵宇No ratings yet
- "物空间"的情感隐喻:当代陶瓷装置"剧场性"特征初探 董金鑫Document2 pages"物空间"的情感隐喻:当代陶瓷装置"剧场性"特征初探 董金鑫Cenzon GaoNo ratings yet
- "触感视觉":一种重新认识电影的理论路径 严芳芳Document8 pages"触感视觉":一种重新认识电影的理论路径 严芳芳Wen WangNo ratings yet
- "元宇宙"中的身体与主体性分裂 曾军Document3 pages"元宇宙"中的身体与主体性分裂 曾军sipaNo ratings yet
- 论洞穴寓言的论点Document8 pages论洞穴寓言的论点xiqvirfngNo ratings yet
- 浅谈创意摄影与音乐艺术带给我们的启示Document1 page浅谈创意摄影与音乐艺术带给我们的启示Pokei KoNo ratings yet
- 依于本源而居:海德格尔艺术现象学文选 ( (德) 马丁·海德格尔 孙周兴 编译) (Z-Library)Document133 pages依于本源而居:海德格尔艺术现象学文选 ( (德) 马丁·海德格尔 孙周兴 编译) (Z-Library)v453389490No ratings yet
- 审美现代性的四个层面 周宪Document10 pages审美现代性的四个层面 周宪Larry ZhangNo ratings yet
- 窗 的美学Document8 pages窗 的美学LeePeiyingNo ratings yet
- 时间维度与感官体验博物馆人类学视域中的观众Document5 pages时间维度与感官体验博物馆人类学视域中的观众nokyee auNo ratings yet
- 在自传与传奇间游走 - 《辛努海》文本研究 李晓东Document6 pages在自传与传奇间游走 - 《辛努海》文本研究 李晓东Hellas SPQRNo ratings yet
- 在自传与传奇间游走 《辛努海》文本研究 - 李晓东Document6 pages在自传与传奇间游走 《辛努海》文本研究 - 李晓东Yanru XuNo ratings yet
- 伯纳姆"系统美学"及其对当代艺术理论的启发 段似膺Document10 pages伯纳姆"系统美学"及其对当代艺术理论的启发 段似膺Chris RenNo ratings yet